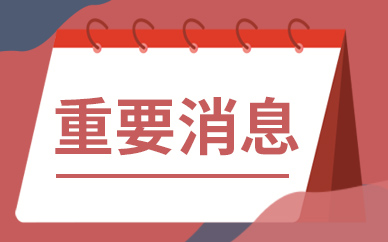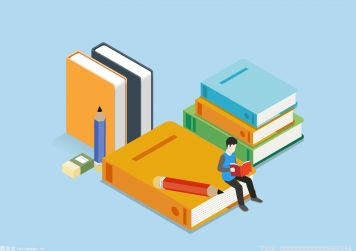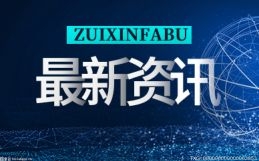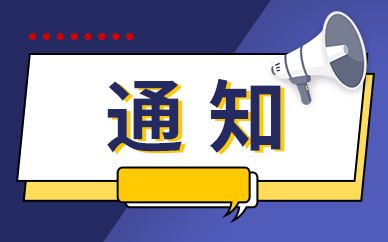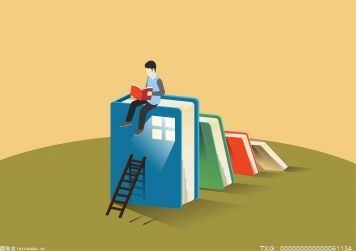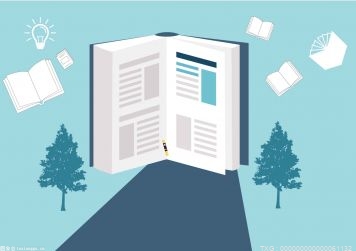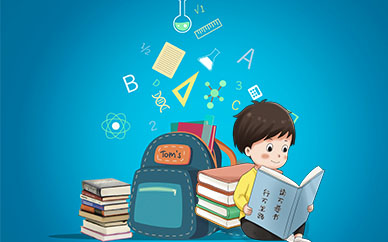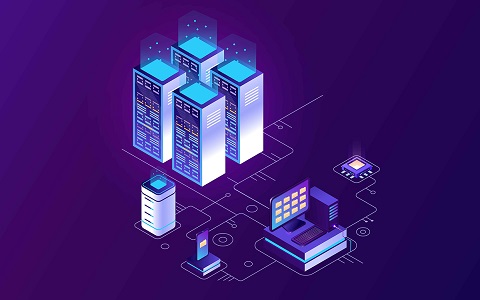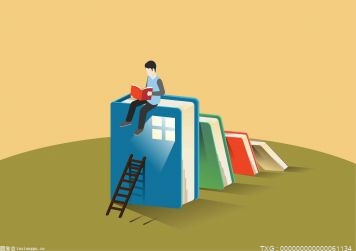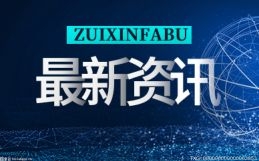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文汐 广州报道托育,成为改善我国人口生育率的重要抓手之一。
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下称“千人托位数”)指标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从发展目标来看,中国要在五年时间内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指标由2020年的1.8个提升至4.5个。
随着全国托育建设的全面铺开,各地也在积极作出响应。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2021年24个万亿GDP城市提出的“十四五”千人托位数目标进行了梳理,其中,成都、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济南、西安、合肥2025年的千人托位数目标高于全国;福州、宁波、上海、北京、苏州、南京、天津、无锡、长沙、南通目标与全国持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显示,2020年,成都千人托位数近2.19个,但提出到2025年将达到8个。
“托育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三孩’生育政策落地实施,以及人民群众‘想生但不敢生’的重要掣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史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进一步指出,做好婴幼儿托育工作不仅事关老百姓的家事,更关乎国之大计。加快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增加托位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迫切亟需的托育服务需求,是“十四五”时期加强和保障民生、实现“幼有所育”的重要任务。
8市千人托位数目标高于全国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2021年全国人口净增长48万,人口发展面临挑战。
“十四五”期间,从供给侧发力,加快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的重要举措,对于鼓励青年人适龄婚育,降低养育成本,减轻育儿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成都、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济南、西安、合肥在“十四五”时期均提出了高于全国的千人托位数目标,依次为8、5.9、5.8、5.8、5.8、5、4.8、4.6(单位:个)。
为何这8座城市目标高于全国?
在史薇看来,其中有两个要素不容忽视,一是发展基础,二是人口变动趋势。从发展基础来看,凡是提出了高于全国目标的城市,可能现阶段的存量托育资源,相对于群众需求而言存在较大缺口,为了弥补这个缺口,自然需要适量增加供给。
“从人口结构和变动趋势来看,如果一个城市或地区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较高,或者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虹吸效应和就业吸纳能力强,有大量外来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涌入,当地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上势必提前作出规划和建设安排,以满足可以预见的未来需求。”史薇指出。
同时,一些城市经济实力雄厚,推进托育建设上的信心更足。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资金充沛,在托育建设上信心更足,也更有底气给予托育机构更多的支持,包括鼓励更多的民营资本、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分析来看,广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已在托育位建设上打下较好的基础。
2020年,佛山和广州千人托位数已经分别达到3.81、3.11。广州作为人口大市,在托位数上也位居前列。根据广州市卫健委数据,截至5月31日,广州市登记注册备案托育机构数为949家,通过备案数为168家,排名均居全省首位,可提供的托位数近6万个。佛山也提出,2022年全市将新增各类托位3000个以上,建设6家以上示范托育机构。
而合肥、深圳二市2020年千人托位数指标还未“破2”,分别为1.6、1.47,但仍提出了较高的目标。
事实上,这两座城市在托育位建设上正在“后起发力”。7月21日,深圳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正式挂牌。截至6月30日,深圳市共有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780家,可提供托位3.59万个,千人托位数2.0个。合肥在6月出台《合肥市托育机构市级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落实对托育机构新增托位等补助。
史薇表示,虽然上述两座城市现阶段的千人托位数还未破2,但既然提出的目标超过全国水平,相信地方政府是结合地方实际做出的科学决策。对于这几座城市而言,未来几年要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重点要放在如何吸引多元社会主体广泛参与上,没有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所谓的增加有效供给只能流于空谈。
托育建设如何提升生育水平?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但我国托育系统仍不够完善、对人民生育意愿的激励作用仍不明显。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早期只有企事业单位有托儿所,但后来改制之后,基本都关闭了。在生育政策逐步放开下,如果托幼设施不够,会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对于大城市来说,员工的流动性比较大,需要提供覆盖范围更广泛的托育服务,应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提供支撑。
“托育政策在众多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中,相对来说投入较小、收益较大,尤其对于大城市而言,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父母不在身边,在育幼上存在困难,若是要雇用月嫂、保姆,也会存在费用上的负担。如果政府能提供普惠性的托育位,对于解决家庭实际上的困难有很大的帮助。”黄文政进一步表示。
董登新认为,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讲,孩子的生养成本、物质和精神上压力的来源主要在托幼阶段,要尽量发挥社会服务设施的支持力量为家庭减压。如果政府、社会在托育阶段能够为人民减负,有利于刺激或提高人口的再生产能力和水平。
事实上,随着全国托育建设的铺开,各地已经有所行动。如北京提出,将在今年下半年启动普惠托育试点工作。安徽省住建部提出,对未配建托育服务设施的新建住宅不予通过验收。深圳出台条例,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两周岁至三周岁的幼儿等。
后续应如何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为解决生育和人口问题提供助力?
“要提升生育率,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改变激励机制,改变社会对于生育的观念。”黄文政向记者表示,目前社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生育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政府应加大支持,使人民摆脱掉视生育为负担的观念,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真正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
董登新认为,托幼是除养老外我国的另一项重大工程,目前来讲,我国养老系统已经相对完善,但托育建设才刚刚起步。“我认为托育体系建设也要相应借鉴养老系统建设的思维和模式,例如在激励机制上,可以借鉴养老机构财政补贴一次性支付的模式。”
董登新进一步表示,完善托育体系,一是要解决数量上的短缺,二是要解决托育机构服务质量评级、行业标准等监管方面的问题。“从托育机构的质量上看,大家普遍更相信公立的托儿所、幼儿园,因为相对来说投入设施较完备、服务质量较好,而私立托育机构质量参差不齐,因为缺乏标准化的监管,存在比较多的问题。”
此外,要切实改善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问题,保障三孩生育政策落地见效,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除托育外,也应完善相应的配套体系。
在史薇看来,重视女性权益保障和推进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是其中的重点。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但同时也是社会劳动的参与者,保障女性权益,首要一条就是要保障女性合法的就业权和生存发展权。
“劳动力市场和用人单位不能因为生育而剥夺女性独立就业、赚取劳动报酬、获得职场晋升以及个人发展的机会和权利。新型生育文化建设重在推动性别平等,要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和陈规陋习,倡导两性共担抚育责任,促进女性工作家庭平衡,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史薇表示。